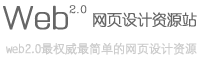西藏启动“检护民生”专项行动
作者:夏奇拉 来源:东来东往 浏览: 【大 中 小】 发布时间:2025-04-05 06:48:04 评论数: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第10条对行政诉讼管辖异议作了相应规定。
[14]同时,市场分配因素自1978年之后进入到旧有的政治系统后并没有发展成为独立的制度因素,更没有改变传统的政治分配机制,市场的发展更多受控于地方政府的斡旋。根据2000年《若干问题的解释》仅非国有企业被行政机关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因此原告不具备起诉资格。

其次,法治监督说强调的是,国家权力在横向层面的分割,通过司法权实现对行政权的拘束,而科层监控说强调的则是,经济分权背景下中央借助行政诉讼制度实现对地方的控制,是国家权力在纵向层面的拘束控制。[43]实际上,最高院的司法政策也悄然发生变化,2000年《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再次提到企业经营自主权的内容时仅针对非国有企业,[44]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问题却似乎被忽略搁置了,而诸多地方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据此认为,只有非国有企业被行政机关注销、撤销、合并、强令兼并、出售、分立或者改变企业隶属关系的,该企业或者其法定代表人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45]使得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纠纷进入诉讼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同样,《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以及《乡镇企业法》中对于企业经营自主权的界定也与之基本类似。Bruce J. Dickson, Wealth into Power: The Communist Partys Embrace of Chinas Private Sector,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8。详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实施前行政审判试点工作中几个问题的答复》,法(行)函(1989)73号,1989年11月20日。
[5] 统计数字可见任建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1991年4月3日。[58] 类似的案件还可见金城江面条厂黄炳尤等53名职工及家属不服金城江镇人民政府企业财产处理决定案[59]以及胡淑英、达宏泉等诉南通市港闸区唐闸镇政府和区工商局侵犯企业法定经营自主权案。多党制、联邦制等制度的组合使得巴西的决策难以快速做出,但这恰恰有助于使决策容纳更多政治力量和选民的诉求,从而增强人们对民主体制的认同。
这种代表观与政党代表观不同,认为只有候选人而非政党才是选民的代表,候选人的去留也只能决定于选民而非政党,因此无论是强调政党领袖对候选人的影响力,还是对变更政党身份的候选人予以惩罚,都与此种代表观相违背。据相关资料统计,政府‘仅仅对自1964年到1984年间的333人的死亡负有责任,远远低于其邻国阿根廷平均死亡数的100倍,也低于智利的50倍。选择增加自主性的制度有利于议员摆脱来自政党领袖的控制。诸如此类的问题在民主化研究领域已经激发了从转型学到巩固学的转变。
这种强烈的反差促使学界开始重新检视之前的研究。伯恩斯切尔也指出,在一些拉美国家,如智利和乌拉圭,在迈向民主的起步阶段就出现了激烈的意识形态分化,纲领性政党在早期就已经出现。

对巴西宪政体制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以梅因沃林(Scott Mainwaring )、奥唐奈(Guillermo A。林茨和斯泰潘就指出,在长期存在的总统制国家中,没有一个国家的国会的有效政党数目超过2。有六位军人直接担任了内阁部长,军队在一些重要的社会事务上仍享有特权,例如,在很多时候可以单方面决定镇压工人罢工,甚至在土地改革的边界划定上也有发言权。[20] 可见,巴西的制度并不是高度分散化的,之前的判断过于简单。
1964年,在逐渐高涨的民粹主义和日益严峻的经济问题的刺激下,巴西军人发动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从此进入军事威权统治时期。Linz)等主流的民主巩固学家为代表。而不幸的是,巴西恰恰集合了所有这些导致纪律涣散的制度。大约只有500名政治家失去了政治权利,而在乌拉圭则是1.5万人。
考虑到它所控制的各种资源,行政部门反过来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此外,民众对军政府时期的反感也成为最终选择总统制的理由之一。

但在巴西这样的国家,虽然早期其政党制度化水平较低,后来却出现了明确致力于改变传统的靠庇护来动员选民方式的左翼政党,如巴西劳工党,而这些新兴的纲领性政党进而迫使其他政党采纳更为明确的纲领,从而加强了政党的社会基础。但正如柴巴布和利蒙吉所指出的:如果我们考察所有范围内的现有总统制政权,我们将发现美国是一个例外,因为它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赋予行政部门立法权力和议程权力,因此,它无论如何也不能代表总统所能做的事情。
这种努力主要从两方面展开:一是挖掘巴西宪制本身有助于提高治理效率的制度安排。 三、对巴西宪政体制的评价 如果以时间段划分,在1995年以前,人们对巴西选择的宪政体制普遍持否定态度,认为只有大幅度改造巴西的政府体制、选举制度和政党制度等才能巩固巴西的民主。但笔者认为从自由民主变成先进民主不应视为民主巩固的一种,因为先进民主指涉的是民主质量不断提升的永恒发展的动态过程,若按此标准,现实中的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包括英美都难以说实现了民主的巩固,这不仅混淆了民主巩固与民主深化,也会大大解构民主巩固这一概念的解释力。因此总统制不适于自然资源富饶的后社会主义国家,但在相对平等且资产流动性高的发达国家,总统制并没有失败的案例,其对民主巩固的影响与议会制别无二致,见鲍什:《民主与再分配》。[5]Scott Mainwaring, Politicians, Parties, and Electoral Systems: Brazil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Comparative Politics 24 (1) (October 1991), pp. 21-43. [6]Scott Mainwaring, Presidentialism, Multipartism, and Democracy: The Difficult Combin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26 (July 1993), pp. 198-227. [7]参见林茨、斯泰潘:《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正基于此,林茨和斯泰潘悲观地指出:在每个决策分歧点上,巴西都选择了最能导致政党分化的规则。
就前者而言,已有不少研究发现,巴西总统尤其是卡多佐任职以来在国会经常能赢得多数的支持,从而能有效推行各方面的改革计划。此外,人们还可能追问,如何理解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评价?抑或,其中哪一种评价更准确地揭示了巴西民主的真相?确实,笔者认为之前以林茨、斯泰潘为代表的主流民主巩固学家对巴西民主前景的悲观态度有待反思,如过于强调治理的有效性对于民主巩固的作用,而忽视了代表性维度和共识民主模式的价值,对宪制的运作逻辑的考察也未能充分深入到具体国家的情境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前后两种视角之间是完全对立的关系。
但是,变革模式导致的军人特权的一度保留以及对文官的影响力,毕竟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威胁着巴西的民主巩固。一般而言,学者主要从制度、行为和文化三个视角来界定民主巩固。
这显然与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倡导的共识民主模式颇为契合。在这种选举制度下,甚至在全国只获得0。
学界的这一转向,使民主巩固学成为近二十年民主化研究的主导方向。[21]就巴西而言,分散化的体制使卢拉所代表的左翼政党有机会进入权力体制,并且在赢得大选之后必须将更多的政治派别纳入决策体制,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左翼的激进化倾向。在他们看来,之前唱衰巴西民主前景的学者倾向于将制度的决策效率视为民主巩固的首要甚至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这显然忽视了制度的合法性抑或代表性对于民主巩固的价值。换言之,基于宪政工程学主动介入的风格,相关的研究更多是站在公正的立法者角度来提出制度变革的建议,但是现实所选择的制度往往是不同政治力量在既定的结构性因素约束下博弈的结果,而后者更需要考虑具体国家的差异性。
总统制的支持者在呼吁民众投票支持总统制时,就特意强调了军政府时期阻碍民众直接选举总统这一点。例如,在组阁时运用联盟手段将其他政党纳入进来以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16]这样,行政部门为各政党领导人提供了用来惩罚那些没有遵循政党路线的普通议员的手段:他们分享官职的机会将被拒绝。
Jorge I. Dominguez Michael Shifter,Constructing Democratic Governance in Latin America,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3。这其中以林茨和斯泰潘给出的综合性定义为代表:就行为层面而言,一个巩固的民主政体之中,没有重要的民族、社会、经济、政治或者制度性的行动者将重要的资源用于建立非民主政体,或者用于寻求外国的干涉从而获取独立。
虽然巴西历史上有总统制的传统,但是鉴于之前总统制容易导致总统与议会之间的冲突进而引发军事政变的教训,起初宪法起草委员会提交的宪法草案是想在巴西引入半总统制,增加议会制的因素,但是因为该草案试图削减总统的任期遭到了萨内尔总统的反对,而军方也认为总统制更有助于加强其对政府的影响力,在此压力下总统制最终被写入宪法。【注释】 [1]当然,民主巩固的概念本身也是学界一直关注且多有争议的话题。
首先,我们应如何看待前面两种看上去截然相反的对于巴西宪制安排的评价?看似前后矛盾的评价是否表明民主巩固学中的制度主义学派所做出的解释是一种事后追溯式的?也即根据现实的民主发展进程来决定对既有制度的评价,这显然与其标榜的站在事先设计的立法者的前瞻性角色相矛盾。还造成国会中有效政党数目过多,难以形成稳定的多数联盟,进而加剧政策僵局。但是根据既有的研究,大体上我们可以列出民主巩固的条件抑或是影响因素:经济发展、文化传统、公民社会、阶级结构、国际因素、文武关系、转型模式、转型前的政体类型、特殊情景问题以及宪制选择等。本文通过考察巴西宪制选择的现实逻辑以及具体的制度安排之于民主巩固的多重影响,反思民主巩固学中的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取向,以期为既有的民主巩固学提供新的知识增量。
这一支持足以使得总统很少能够在投票中被打败。1988年新宪法最终选择总统制,与军方的介入密切相关。
本文选取巴西这一经典案例对此予以深入考察。就后者来说,正如鲍什(Carles Boix)所批评的:研究民主化的新制度主义学派并未考虑既已存在的经济、社会条件,在他们看来制度似乎是在社会真空中运转的。
本文对巴西民主巩固的诊断也遵循这一判断。积极巩固指的是从选举民主转到自由民主抑或是从自由民主变成先进民主,前者意味着完成民主,后者是深化民主。